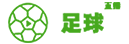一、中国男足可以冲击2022年世界杯吗
近日,中国男足在塔什干本尤德科体育场以0:2不敌乌兹别克斯坦,全场只有两脚射门,威胁进攻寥寥无几,对手多次击中门柱和横梁,4场比赛只积1分,12强赛生死战失利,国足好像又只剩理论希望了。面对如此糟糕的战绩,国足主帅高洪波在赛后宣布辞职。
很多人认为,中国出线希望小,开始期待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但是,客观条件方面,2022年世界杯应该是中国冲击难度最大的了。
下面让我们来分析一下: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东道主卡塔尔队直接占用一个亚洲名额,亚洲只有3.5个名额。澳大利亚、韩国、日本、伊朗等亚洲诸强将争夺这3.5个名额。这意味着,正常情况下,凭借实力代表亚洲参加世界杯的澳大利亚、韩国、日本和伊朗当中的一支强队都会被淘汰或者参加附加赛。
有人可能会举例2002年的世界杯,日本和韩国同样也直接占用了2个亚洲名额。但是,客观实力上,正常情况下,日本和韩国也能凭实力进入世界杯。而卡塔尔凭实力是没法进入世界杯的,所以,卡塔尔参加世界杯,那么,澳、韩、日、伊当中将有一支强队被淘汰,或者参加附加赛。
中国在冲击2022年世界杯的时候,应该会出现这种情况。随着,中超联赛持续的火爆和大牌外援持续的加盟,中超联赛中中国球员的实力得到了进一步不断的提升。以恒大足校、鲁能足校、各队青训等为代表的中超土豪们的青训在那时收到了丰收的成果,培养了大量的人才。以张玉宁、林良铭、杨立瑜等为代表的97国青海外留洋球员的部分人成功在欧洲联赛立足。
本国联赛中国球员实力的强大、优质青训成果的产出、出色的海外球员,使得中国国家队的实力相比以往空前的强大。最后,形成了中国和澳大利亚、韩国、日本、伊朗竞争3.5个名额。实力强大的中国队战斗到了最后。但是由于这是冲击世界杯难度最大的一届,澳大利亚、韩国、日本、伊朗这亚洲豪强们的实力又太过强大。
最终,中国和另外一个强队,个人觉得是韩国队,被淘汰,澳大利亚、日本和伊朗直接进入世界杯。中国或者韩国参加附加赛,因为附加赛的对手通常是中北美或者南美洲的球队,所以,亚洲球队进入世界杯的希望很小。所以,中国又如1997年,“史上最强的中国队”距离法国世界杯只差一步一样,距离再次进入世界杯只差一步。
大家觉得呢?2022年世界杯是不是客观条件上中国或是其他亚洲球队冲击难度最大的一届世界杯?
二、为什么中国男足踢不好
这是个很大的问题了,高票的几个答案说的都不错,我仅仅做些补充。男足踢得好不好和所谓的羞耻心关系真的不大。
有太多的人像题主这样单纯的以为中国男足踢不好是因为他们不努力没羞耻心。这是把问题想得太简单了。意志力、羞耻心、爱国等等,这些精神层面上的东西对于一个运动员固然重要但是仅仅在双方势均力敌的时候这些精神层面的东西才会起作用。如果这些精神层面上的东西是最重要的那么朝鲜队应该是世界上最强的球队。可笑的是还有不少人喜欢吹朝鲜。但一个事实是,在成年国家队层面上,国足谁都敢输但几乎见一次朝鲜灭一次。有一支优秀的国家队得满足以下的条件:大量的足球人口、科学的训练、良好的职业环境。可惜这些在中国都没有。这种环境下出来的球员就算再努力也是无济于事的。
中国男足为什么踢不好,直接原因很简单。@吴潇雄
给的答案已经很好了,就是足球人口太少。我们从来都不是从13亿人里挑11个人踢球,而是从1万多人里。我们的足球人口不用跟足球强国比,甚至还不及越南!所以说现在国家队能踢得过越南已经不错了。这不是黑,真心的。说明咱们国家虽然足球人口不多但相对来说质量还是挺高的。
中国足球的问题在于体制,不在于球员。所以我从来不会去指责某一个球员。因为每个能成为职业球员的人都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这些努力包括他们个人的努力也包括家里的努力(哪方面大家懂得)。可能很多人觉得男足球运动员很幸福,没什么成绩还工资那么高。但你们有没有想过中超的球队加上中甲几个强队,20几个队也就几百个人高薪。那剩下的1万多人你们关心过吗?
我倒是认识一个保安大哥,20年前他有机会去踢甲A但是需要给10万块钱。20年前的10万是什么概念大家也懂的,他家里没钱又没读过多少书所以呢就当保安了。并不是每个职业球员家里都有钱,为了培养一个球员倾家荡产的也有不少。
即便有些球员综合素质确实很差我想的也不是去指责这个人而会去想为什么这样的人也能进国家队,这就是背后的体制问题了。其实不仅仅是足球,其他项目的体制很完美吗?事实上在举国体制的大背景下几乎所有体育项目的发展都是畸形的。足球虽然已经职业化但仍然没有完全摆脱举国体制的影子。足球有的问题乒乓球、举重、体操也有。但是因为那些项目的成绩太好了所以就没有人关心背后的问题了。注意举国体制只对职业化程度低的运动项目有效!
一个能进国家队的足球运动员所付出的汗水未必比一个乒乓球世界冠军少。因为足球运动员面对的是一个高度职业化的世界。而乒乓球运动员所面对的国外运动员,大多是训练水平和时间都难保障的运动员,甚至还有业余运动员。
记得奥运会期间有个段子说:“有一群运动员,他们的工资大多来自企业赞助,很少花纳税人的钱。他们组成的队伍虽然屡战屡败,但依旧坚持着。他们最好的诠释这奥林匹克精神,他们是中国男足。”其实我觉得这不是恶搞,这是很有道理的一段话。足球在我国是职业化最高的,球员基本可以脱离体制生存,他们工资虽然高但挣得不是纳税人的钱!
说了这些就是希望大家能多体谅一下运动员。不管什么项目,能进得了国家队的人都挺不容易的。
三、中国足球守门员是哪个
李惠堂,1976年联邦德国一家权威性的足球杂志曾组织过一次评选活动,将中国的李惠堂与巴西的贝利、英格兰的马修斯、西班牙的斯蒂法诺和匈牙利的普斯卡什并列评为"世界五大球王"。但笔者认为称李惠堂为"亚洲球王"似乎更合适,因为在亚洲以外的赛事中他并没有取得过骄人的成绩,他的进球含金量不高。
李惠堂,字光梁,号鲁卫,1905年出生于香港。其父李浩如,系广东省五华县人。李惠堂4岁那年,随母亲回到家乡五华县锡坑乡老楼村居住。在那里,这个天性喜爱足球的孩子,把家门口的狗洞当成了练习射门的目标。由于家境贫寒,买不起足球,他只好用柚子当球光着脚丫子苦练,上学和放学回家的路上都盘球走路,这不仅磨练了他的意志而且提高了带球技术。经过几年的锻炼,他的身体日见壮实,球技过人。
10岁左右,李惠堂回到香港。 1921年考入足球运动比较普及的皇仁书院,接受了比较系统的足球训练。
1922年,年仅17岁的李惠堂被选入香港最有名气的足球劲旅--南华队,出任主力前锋。他身高1.82米,速度快,动作敏捷,控球技术尤为出色。球在他的脚下,对方两三个人围上去也难以抢走。他的射门技术更是令人叫绝,不管什么位置、什么角度,他都能左右开弓,球出如矢,力拔千钧。他的倒地卧射更是一大绝招。
1922年夏天,李惠堂代表南华队参加香港甲级足球联赛,出任左内锋,因其球艺娴熟刁钻,出神入化,常有惊人之举,香港球迷称之为"球怪"。
1923年5月,李惠堂第一次代表中国足球队参加日本大阪举行的第六届远东运动会,中国队获冠军。18岁的李惠堂在4场比赛中初露锋芒,名声大振。从此开始了他献身足球的光荣生涯。
同年8月,李惠堂随南华远征澳大利亚,与全澳冠军新南威尔士队交锋。开场仅5分钟李惠堂就梅开二度,这场比赛他一人独中三元,轰动了整个澳州。澳州当局专门授予他金质奖章。香港当地报刊以特大号标题,称李惠堂为"球王",并有"万人声里叫球王,碧眼紫髯也颂扬"的诗句。
20年代的上海,足球命运完全操纵在外国人手里。1925年,年轻的李惠堂怀着强烈的爱国热忱,与自己青梅竹马的邻居廖月英从香港来到上海,决心要与外国球队较量。
李惠堂在上海期间,正值自己足球技艺的巅峰状态,由于球艺出众,22岁即被上海复旦大学足球队聘为教练。随后,又参加上海乐华足球队,战绩显赫。1926年,李惠堂率乐华足球队参加上海举行的"史考托杯"足球赛,以4∶1的悬殊比分大胜蝉联9届冠军的英国猎克斯队,首开上海华人足球队击败外国球队的记录,使李惠堂在绿茵场上的威望大增。洗雪了"东亚病夫"的耻辱,为中国人民出了气,为中华民族争了光。
1927年,李惠堂所在的球队如日中天,相继荣获西联甲组联赛、首届高级杯赛和中联甲组联赛的冠军,李惠堂成为大名鼎鼎的"一代球王"。同年,李惠堂率乐华队在远征东南亚国家中,屡建奇功,特别是率队出战菲律宾,战绩彪炳,载誉而归。
李惠堂球风正派,脚下功夫深。一次,他在与英国海军球队比赛时,球刚过中线,就拔脚怒射,球竟穿过好几个英国选手的人丛像精确制导的导弹一样钻进网窝。还有一次与西人联队对阵,他一人从后场盘球,接连晃过四五个前来阻截的对手,一直把球带到对方禁区,从容起脚,把球攻入门里。这种球艺堪与马休斯、贝利和马拉多纳相媲美。
李惠堂为国家队做出了突出的贡献。1923年入选中国队,分别于1923、1925、1930、1934年参加了第六届、第七届、第九届和第十届远东运动会足球赛,4次都为中国队夺得冠军。
李惠堂1931年返回香港,加入南华足球队并担任队长。1931年,国际奥委会承认"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为国际奥委会会员,使我国体育健儿有机会与其他国家的足球运动员进行切磋、交流。
由于当时的国民党政府财力困难,1936年为参加柏林奥运会足球赛,李惠堂和足球队只能自筹资金,提前两个多月出发,靠沿途比赛的门票收入作为参加奥运会的费用。李惠堂和队友沿途进行了27场比赛,取得了23胜4平的战绩。他们省吃俭用,一路风尘赶到柏林。但由于一路征战,球员已疲惫不堪,到奥运会比赛时,以0比2负于英格兰队,首轮即遭淘汰。
1939年,李惠堂随香港南华队远征南洋,在和马来西亚槟城联军队的首战中,南华队以11∶0大胜。在这场比赛当中,35岁的李惠堂雄姿依旧,频频带球过人开弓劲射,独入7球。一次,在和一支外国队的比赛中,李惠堂一记强有力的劲射,正中"洋将"守门员怀中。守门员收腹不及,顿时倒跪在地。
香港沦陷后,李惠堂不愿做亡国奴,于1941年以借到澳门比赛之机,辗转回到内地。他与家乡人组建了五华足球队。在家门口贴上了一幅对联:"认认真真抗战,随随便便过年。"
1942年,李惠堂到梅县与强民队对垒,结果以1∶3"礼让"强民。第二年,李惠堂邀请香港甲组高手,以"航建队"名义,与强民队比赛。通过这两次比赛,对"足球之乡"梅县的足球运动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尔后,李惠堂到桂林组织广东足球队,参加所谓四省"元首杯"足球赛。他先后在重庆、成都、自贡等地作表演赛和义赛,筹集款项,救济战孤、难民,支持抗日救国。
1947年,李惠堂已经45岁,他在香港参加埠际赛(沪港杯赛的前身),他射出的一个点球被扑中,这场比赛是他的"挂靴之战"。
1948年李惠堂作为教练率中国足球队参加第十四届奥运会足球赛,同年获国际足联国际裁判证书,成为中国第一位获得国际裁判资格的人。1954、1955年率中国台北队夺得第二届、第三届亚运会足球赛冠军。
1954年李惠堂当选为亚洲足球联合会秘书长。1965年,他当选为国际足联副主席,成为在国际足联获得最高职务的中国人。
1966年李惠堂担任亚洲足球协会和世界足球协会的副会长,在世界足坛享有很高的威望。1976年在联邦德国足球杂志组织的评选活动中,他被评为世界五大球王之一。
1979年7月李惠堂因病在香港去世,享年7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