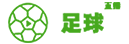一、均势外交英国外交政策
在维也纳会议这一时期,英国实行均势外交的具体表现是当欧陆基本稳定时,英国便摆出“超脱”的态度,不干涉欧洲事务。当大国力量均衡被打破,均势受到威胁时,它就扶弱抑强,维持均势。
维也纳会议上,英国的自身利益得到了保障,欧洲大陆上建立起了较稳定的多级构势。从这时起,英国的主要外交目标就是维护维也纳体系形成的欧洲均势,积极开拓海外霸权。其外交政策逐渐倾向于对欧洲事务少干涉,少卷入,直至孤立。当欧洲列强打着“欧洲协调”的旗号到处干涉革命时,当时的外交大臣卡斯尔雷就声明:“逢欧境领土平衡遭到破坏时,彼(英国)可有效干预,但于任何抽象问题,彼定位欧境最无可能冒险投入之政府,吾国无意亦无法依抽象性戒备原则即付出行动”。为缓和原则上的分歧,卡斯尔雷曾建议各国见面或召开正式会议检讨欧洲局势(欧洲会议制度),但是英国对这样的“欧洲政府制度”极为排斥。卡斯尔雷的继任者坎宁立即切断了卡斯尔雷对欧洲会议制度的最后几个管道,不管它们如何间接。坎宁呼吁“言行均保持中立”的政策,他说:“不要为愚蠢的浪漫情绪所惑,误以为我们只手可以重建欧洲”,“我国与欧洲系统关系虽密切单兵意指没有状况我国便须应邻国关切之召请,而致入纷扰之中”。卡斯尔雷及坎宁都对神圣同盟采取不合作态度,尤其是坎宁,他认为欧洲君主国联合霸占欧洲成为更现实的危险,这样会使英国陷于孤立。他们反对神圣同盟对西班牙革命,拉美独立运动和希腊革命的干涉和革命。
殖民扩张到了三十年代的帕麦斯顿政府凭借英国的“世界工厂”和海洋霸主地位,以自由主义之名开始在全球海洋和大陆实行殖民扩张政策,对欧洲事务兴趣不大。帕麦斯顿崇尚均势外交,善于利用各种事件和环境促进英国的利益,维护均势。1830年比利时起义,英国既担心东欧三个保守君主国干涉,又怕法国乘机扩张势力,控制比利时。于是帕麦斯顿同法国合作以阻止俄国,普鲁士,奥地利可能的干涉,还以战争威胁迫使法国军队撤出比利时,最后以“欧洲协调”方式通过了“伦敦公约”,保障比利时的独立和中立地位。欧洲的均势格局基本保持,而一个对英国友好的比利时对英国的安全和商业利益是很有好处的。
1848年法国二月革命爆发后,帕麦斯顿政府拒绝由俄国提出的由俄英奥普联合干涉二月革命的计划,因为它从一贯的均势政策出发,并不认为法国队其构成重大威胁。出于相同原因,帕麦斯顿政府对1848年中的德意志革命,奥地利革命,意大利民族运动等持观望和调停态度。俄国武装干涉但此时,沙皇俄国膨胀成为英国均势政策的主要威胁,1848年革命俄军帮助奥地利队匈牙利革命进行了武装干涉,俨然成为欧洲主宰,欧洲宪兵。俄国以圣地保护权为借口,扩大在土耳其的势力,占领多瑙河两公国瓦拉几亚和摩尔达维亚,其实质是夺得君士坦丁堡和黑海两海峡的控制权。于是英国联合法国,扶植没落的奥斯曼帝国于1853年在克里米亚战争中大败了俄国。俄国在巴尔干的扩张被制止,黑海中立化,俄国不得在黑海沿岸建设海陆军设施基地,土耳其作为抵御俄国的缓冲国被保留了下来——所有这些有利于英国在近东,印度和远东的扩张,英国对欧洲的控制加强,而维也纳会议所确立的五强均势仍然保持了下来,对英国来讲无疑是个大的胜利。
光辉孤立政策克里米亚战争后,欧洲均势又得到恢复巩固英国对欧洲大陆奉行更为彻底的不干涉政策,即光辉孤立政策(splendidisolation)。帕麦斯顿内阁不愿介入于1864年的普丹战争。格莱斯顿政府对普法战争作壁上观,他们认为普鲁士的崛起对英国的利益不会构成真正的威胁,或者相反,一个强大的德意志可以作为抗衡法国的堡垒,尤其当时法国是苏伊士运河的主人。
普法战争以后,欧洲局势急剧变化,德国一跃成为欧陆首强,法国念念不忘复仇雪耻。孤立法国,防止力不能及的两线作战是俾斯麦制定的外交政策的总目标。俾斯麦大利开展结盟外交,英国是其极力追求的对象之一。英国的主要对手是法俄,与俄奥意的利益一致,但是为了保持行动自由,与1870年11月,1879年10月,1891年5月三次拒绝了俾斯麦和意大利要求加入同盟的要求。固然英国在1887年同奥匈和意大利订立了《地中海协定》以在近东对付俄国,在地中海对付法国,但是该协定并没有发展成为附带固定军事义务的结盟状态。索尔兹伯里在给英王的报告中指出:“在拟定英国照会时保留了判断在各种场合是否需要与意大利政府合作给与军事援助的绝对自由”。就这样英国在19世纪后半期独立于任何同盟之外,以“光辉孤立”自豪,操纵欧陆的平衡。直到20世纪由于客观形势的发展,英国不得不放弃孤立政策而与他国结盟,同时也失去了行动自由和操控欧陆均势的能力。
政策理解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对“不干涉”“光辉孤立”政策的理解。这并意味着英国会完全置身于欧洲事务之外,英国只是利用列强间的矛盾,使它们相互牵制以维护均势。只要不外危及均势,英国就采取“超脱”的态度,均势一旦遭到破坏,它通常给同谋求霸权相抗衡的一方经济外交支持,支持弱小的一方抵抗强大的一方,充当平衡者。例克里米亚战争中,应打败了俄国,而在法德战争危机中英又联俄抗德。从这个意义上讲,“孤立”理解为一种有限责任,一种行动自由也是有道理的。1896年索尔兹伯里提出英国不应该参加固定的联盟,应保持行动自由以操纵欧洲均势,这才是光辉孤立政策的本意所在。
扩展资料
大国为谋求霸权而采取的一种外交手段。“均势”是对立大国或集团之间力量对比未出现一方占有优势的客观反映。均势外交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是从 16世纪欧洲的民族国家争夺欧陆和海上霸权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最早推行这种政策的是英国,16世纪初,英首席大臣 T.沃尔西初支持西班牙同法国作战,但当西班牙取得支配欧洲的优势时,转而倾向法国。
二、英国外交
英国自近代以来其外交政策一贯恪守“均势原则”。由于英伦三岛远离欧陆以及其在世界资产阶级工业革命中的领先地位,促成了英国在许多欧洲重大问题上能够“超然物外”。18—19世纪,英国以其拥有的无可匹敌的政治、军事及经济力量,傲视群雄、睥睨众小。凭借着“重海洋、轻大陆”的海上霸权战略,在对欧陆外交政策中奉行“光荣孤立”,推行“均势外交”,不与欧陆任何强国建立联盟,同时保持英国对欧陆事务的充分发言权。与美国的“孤立主义”不同,英国的“光荣孤立”还隐含着对欧洲霸权及影响的重大含义。
尽管出于现实需要,英国在这一时期也曾有过与欧陆国家的联合,如19世纪初为战胜拿破仑帝国而结成的数次“反法联盟”等,但这充其量不过是英国推行其均势政策、现实主义外交的一种策略,无法从根本上动摇英国外交传统的“均势原则”。英国“均势外交”中的诸多因素,如领导责任、着力幕后控制、强调纵横裨阖、灵活机动以及制衡均势等现实主义外交精神影响深远,深深植入其外交实践的骨髓,贯穿了英国各个历史发展时期,构成其对外政策基础的核心。
如果说“光荣孤立”政策反映了英国近代以来所拥有的强大国力以及重大国际影响,那么,19世纪末20世纪初其外交政策的变化则反映了其国力的衰退以及国际环境的变化,随着美国、德国崛起,英国的欧洲霸主地位遭遇空前挑战。19世纪后期,英国放弃“光荣孤立”政策而与法、俄结盟,目的在于维系摇摇欲坠的旧世界秩序,由此,英国推出“有限责任”政策代替“光荣孤立”政策。作为后者的延伸,“有限责任”政策更强调英国作为欧洲大国对欧陆事务所担负的道义与现实责任,而这种责任大多关系英国的切身利益;同时该政策也强调了英国历史与地理的特殊性,突出其责任的“有限性”。事实上,“有限责任”政策并没有放弃其传统的“均势原则”,所不同的是,正是由于严格遵守“均势与制衡”的外交传统,在外交实践中,英国采取“举而待发”的灵活策略,借以维护欧洲相对“均势”格局。
从20世纪初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有限责任”政策主导了英国外交实践。英国在一战中参加协约国对同盟国作战,体现了英国“有限责任”政策的威慑性。一战结束后,在欧洲力量重组及世界秩序整合的力量角逐中,英国的“有限责任”政策在外交实践中更体现了其机变与灵活的特点,在对待法国的战后欧洲霸权政策上,英国视责任与距离并重,假仲裁者之手积极扶持德国,牵制法国。20年代的德国赔款问题、“洛迦诺公约”等都成功地体现了英国外交政策中“均势与制衡”的精神,这使英国“有限责任”政策在实践中高屋建瓴,游刃有余。然而,随着30年代德国法西斯力量扩展,英国的“有限责任”政策在法西斯的战争叫嚣下显得捉筋见肘、力不从心,对这一时期的英国来说,它既缺乏介入欧洲事务的决心,又缺乏介入的手段(注:J.拜理斯:《实用主义外交:英国与北约的成立,1942—1949年》(J.Bayliss,The Diplomacy of Pragmatism.Britain and the Formation of NATO,1942— 1949),俄亥俄1993年版,第一、二章。)。在德国法西斯的一系列军事冒险与扩张中,英国采取了绥靖与遏制并行的政策。“有限责任”政策就象一部严重缺乏润滑油的破旧机器,无法有效运转。1939年3月,德国吞并捷克斯洛伐克,全面改变了欧洲力量对比,英国外交政策出现新变化,但随后的“张伯伦革命”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英国外交实践的颓势。英国对东欧、南欧以至北欧部分国家提出安全与领土保障承诺,实质上是“有限责任”政策失效后英国遏制、威慑德国的战略调整,对英国来说这是极其冒险与卤莽的,因为它缺乏必要且强有力的政策支持与实力来承兑其诺言。
1939年9月,二战爆发,英国“有限责任”政策走到了尽头。在丘吉尔战时联合内阁的领导下,英国外交政策出现新的转变,“联盟政策”明确成为其外交实践的主导方针。该政策到二战结束初期逐步发展定型,成为英国战后外交战略的核心。英国外交政策这一转变原因是多方面的,它既起因于二战中英国的进一步衰落,更因为战后美国的崛起及其世界主义政策全面改变了旧世界力量格局与分布,迫使英国不得不改弦更章,适应世界新格局的发展趋势。然而,这一转变过程的实现是异常困难的,因为虽然“在二战期间英国外交政策的重新定向就已开始了,但直到战争结束,在英国外交政策的制定者中间仍存在着巨大的思想混乱”。
新“联盟政策”与以往不同,英国不再高高在上、俯视欧洲事务,而是以更加平等的“伙伴”身份与欧陆国家平等相待,加强相互间军事、政治合作。然而,英国外交政策的转变仍存在着其称霸欧洲的政策意图,而且在政策制定和外交实践中也存在着浓厚的美国情结。尽管转变的直接原因是二战的险峻形势使然,但就其实践的结果来说,仍然是为了建立英国领导的新的欧洲和世界安全模式。
由此可见,英国近代以来其对外政策的三个变化,尽管其外在形式多种多样,在外交实践中侧重点也各不相同,但是其发展、演变的连续性与继承性是显而易见的,无论是“光荣孤立”,还是“有限政策”抑或“联盟政策”,追求英国的欧洲霸权及影响,维护“均势”、提倡“制衡”的外交精神是一脉相承的。作为英国战后外交政策的产物,西欧国家政治军事联合的新安全模式,不可避免地要打上“现实”与“均势”的烙印。
三、英国外交四个步骤
英国自近代以来其外交政策一贯恪守“均势原则”
由于英伦三岛远离欧陆以及其在世界资产阶级工业革命中的领先地位,促成了英国在许多欧洲重大问题上能够“超然物外”。18—19世纪,英国以其拥有的无可匹敌的政治、军事及经济力量,傲视群雄、睥睨众小。凭借着“重海洋、轻大陆”的海上霸权战略,在对欧陆外交政策中奉行“光荣孤立”,推行“均势外交”,不与欧陆任何强国建立联盟,同时保持英国对欧陆事务的充分发言权。与美国的“孤立主义”不同,英国的“光荣孤立”还隐含着对欧洲霸权及影响的重大含义。